梦幻西游手游科举答题器,潮汕话金榜是什么意思?
答,金榜是指古代科举考试已是殿试考中的人上榜公示的名单即称金榜题名。如举人,探花,榜眼,壮元,上榜就是待等放官上任。所以这张榜含金量比金还高。现在有人称高考录取已说成金榜题名,其实不可比,比例不同,出路不同,
秀才举人进士在古代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学历?
秀才若是211的话,那么举人已经是等同于完成大型国考的“预备公务员”了,有机会在中央部门任职,回到地方也是很有潜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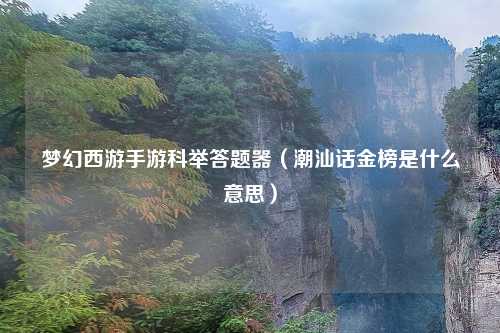
这已经不仅是学历的问题了,而是人才价值的问题。古代科举更加强调人才的价值,而不是学历高低。
接着,如果还能继续考最后一级殿试,一旦成为进士,若是足够排前,直接会被授予官位(往往是从九品到从八品),这在现代的角度来讲,那就等同于直接给予“行政级别”,第一名进士状元给予一个“处级”都是有可能的。
而这些进士学者,若是留在朝廷中央,他们会被分配到京城的“学士殿”(翰林院),这个学士殿就是朝廷文官的培养地,也同样是人才的聚集地。站在如今的角度来看,地位等同于如今的“两院”(工程院、科学院),古代进士已经可以等同于两院院士了,这个身份已经不是学历范畴问题了。
如果选择不在朝廷中央,在宋明两代,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后,就立即报道出去地方历练,职务一般都是“副县及”或者“县级”(县令或县丞、县尉),主要看地方,要是江南发达的县区,一二把手的位置可能就捞不到了,但即便如此,外放为官也是正科级乃至副处级保底的。
宋明两朝科举最为繁荣,但两朝科举的概念不同唐宋时代的秀才和举人与明清时代的不一样,唐宋时期,秀才是对所有准备考科举的学子的称呼,到了宋代最为明显。而明代则是要通过童试之后,也可以理解为受过了一定的“全日制教育”之后,才能被称为秀才。
而举人,在唐宋时意思是被举荐到某一级别考试的学生。例如北宋欧阳修,他中进士那年,就是其岳父举荐他进入国子监考试,到了明代这种就叫监生。而明代的举人则是需要考过了第一重地方的乡试之后,并且获得了功名,才能称之为举人,俗称“老爷”。
宋代的科举是繁荣的,但也是和如今的“学历”制最不挂钩。
因为古人坚信学无止境,在宋代,有苏洵、柳三变这样没有进士之身,却才高八斗、享誉大宋朝的文人,有时候功名更是象征着“政治前途”,而不是如今的知识等级。
两宋时期,为了维护民间的稳定,两宋取士高达十一万人,而且两宋取士,还是沿袭了唐朝的“九科”,其中也是以进士科为主,因为考了进士科就可以为官。但其他的例如明算科,这个典型就是考数学、天文方面的,一进去就是个科学人才,往往会被分配到“天文局”,唐代是叫太史局、宋代称之为“司天台”,有官位在身,但是不主政。
而这也被认为是冗官的根源。
到了明代,科举难度大大增加,明朝统治者搞出了个“全日制教育”,也就是童试之前需要有一定的“上学经历”,经过三次考试(童试:县试、府试、院试),才能称之为秀才,不过在明代,一些情况下通过了县试也能算是秀才,所以明代的科举也有地方差异。
按一般情况来讲,如果把秀才当成211全日制本科学历来看,那么其实考到府试的情况下,就等于学士学历了,再到考完院试,就已经等同于拿到了“211硕士研究生”的身份了,也有资格被称为“生员”,这个生员就是有资格继续去进行乡试,顺利的话,再去进行会试,也称为礼部试,即便是卡在了礼部试,但考到了这个级别,就已经很厉害了。
整个明代科举取士才两万多人,是宋代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点,而明代的人口只会比宋代更多,这个举人的含量可不低,回到地方小县城,那都是可以光宗耀祖上百年的。
明道考完了殿试,就会有一种分配,叫做“观政进士”,这个观政的意思就很简单,等待分配,有可能分配到中央,但绝大部分都是分配到地方任县级的一二把手。在形式上和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分配类似。而更厉害的还可以参加一个“庶吉士考试”,这个庶吉士考试一般都是从进士里再选厉害的出来考,比进士更牛。
考完之后,考的不错的就可以分配到“翰林院”。
要是了解明代的翰林院,就知道这个翰林院就是个国家领导人培养机构,在宋代也是如此,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都在翰林院待过。而明代的大儒方孝孺,明朝续命神话张居正都曾在翰林院待过。
所以宋代的科举与明代的不同。
宋代的科举人才在我国“进士历史价值”角度来讲,属于通货膨胀那一款,实在太多了,可能一个进士在县政府混个判官都混不到。而明代说不上是通货紧缩,但相对来讲,明代的科举人才更受尊重,有“观念”加分,有些秀才在胡同里待着,一辈子啥都不做,照样会有人养他一辈子,这就是理学兴起后对这些读书人的影响。
宋代发展至明代:技术型进士逐渐被政治性进士所取代现代的知识被细分,被多元化,每一个专业都有共同的学历等级,但不意味着每一专业都会从事政治工作。
其实在唐代时,唐代的社会也是如此的。
自唐太宗起,就注重人才多元化发展,之所以要比后来明清时期的风气更加开放,是因为唐代并没有把儒学推到那么高的一个境界。除了儒学以外,明代文人其实主修“道德”,而不是实用性,正如明代经常说的那句,以锦绣文章来击败敌人,但实际上大家知道这不可能的。
“凡明数造术、辨明术理者为通,全通者及第。”
唐代这种对于知识的理性是很难得的。
给予专业人才及第,这是促进社会多元的重要基础。但到了宋代,这种趋势就逐渐减弱了,因为儒学的兴起,政治文人的势力因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越来越大,他们占据科举话语权,他们只懂道德文章,你要是搞个数学、物理去考试,他们也看不懂,因为考官都是学道德文章的,。
例如苏轼,王安石等人,他们能出名就是因为文章写得好,道德好。
而王安石后来执政,对这种现象有所改善。先是弄了三舍法,在基层把教育给细分好,三舍法对于明代科举是有启示作用的。除此之外,王安石对于宋代这种只崇尚“道德文章”的行为十分排斥。
于是在教科书上进行改革,除此之外,他为了变法更加符合实际,与宋神宗商量改变“取士”倾向,殿试的问题就开始问“策论”,就一个现实的问题来向考生索要方法。这其实就和一些现代的高级公务员考试十分相像了。
再说回宋代科举中关于“技术型人才”的减少。
因为贸易的涌入,大量外来文化、技术填充了宋代的科技需求,因此,取士其实已经高度向政治人才倾斜,几乎没有什么数学家、科研人员有官位在身,翰林院也不再是“技术人才”的储备地,而是朝廷官员的预备营。
那么到了明代就不用说了,就方孝孺的地位而言,可以看得出明代对“儒”的痴迷。
姚广孝说方孝孺一死,天下读书人绝矣。
虽然方孝孺是一个极其有造诣的文人、官员,但是把他当成一个社会人才发展的主流模版,这种危害不亚于海禁所带来的闭塞。
而明代也出现了很严重的“教育内卷”。
先是基层的童试,再到乡试、会试、殿试、庶吉士,最重要的是,最终取士的人并不多。这就把社会人才全部压迫在道德文章的思索上了,八股文如何诞生的?正是这种教育内卷所导致的,这种教育内卷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科举取士的“级别”和现在学历的差异要说古代的科举“学历”和现代学历有多大的相似性,其实是没有的。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古代上千年人才选拔制度,的确是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科举自从进入了“八股文”的时代之后,已经走向了“低效化”。
“为官”思想根深蒂固,这形成了社会局限性的恶性循环。
现代则是不同,职业多元化、专业多元化。学历可覆盖认证的专业极多。而这也是现代学历和古代科举的学历最大的区分。
科举不求学历,只求能够为官。现代学历建立在社会多元化上,学历有着强大的证明作用,而我国现代也有官员本身是高学历学者型人才,其实既是部门官员,又是技术、知识人才,这才是真正的“进士”,他们也是现代的进士。
例如钟南山院士,他本就是医学人才,以医获得人民的尊敬,这和明代清代强调“尊儒”的本质不同。再如袁隆平院士,他的杂交水稻解决了世界粮食问题,其实说白了,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将知识和社会贡献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东西。
而科举则是“功名即贡献”,进士则伟大。
所幸,我们走出了这个教育的陷阱,正走向光明。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我们常把考试落榜称为名落孙山?
考大学沒考上,叫什么,“名落孙山”,这是人们常用来指参加考试沒有被录取的一个成语。
意思知道,但有些人对成语中“孙山”的意思不是很理解,有人认为是一座山的名字呢。
成语中的“孙山”可不是指的山,而是一个人的姓名。它出自宋代《过庭录》:
“吴人孙山,滑稽才子也。赴举他郡,乡人讬以子偕往。乡人子失意,山缀榜末,先归。乡人问其子得失,山曰:‘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故事讲的是发生在宋朝,有一才子,名字叫孙山,这个人很幽默,很善于讲笑话,周围的人就给他取了个“滑稽才子”的绰号。
有一次,他跟一个同乡的儿子同到京城参加举人的考试。
等到考完发榜的时,它的名字在榜文上列倒数第一,不管怎么说也是榜上有名吧,而那位同乡的儿子,连榜都沒上。
回到家里,同乡来问他儿子考的如何,孙山觉得不好直说,于是就张来了两句诗:
“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
他的意思是我孙山县最后一名,你儿子的名字还排在我孙山名字的后面。
后来,人们都把参加考试,没有考上或被录取,叫做“名落孙山”。
注:图片来自网络
历史上有哪些真实的祸从口出的事件?
台湾有一个真实的案件,五岁男孩无意间说出:「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长辈吓得赶紧报了案。人们说小孩子才不会撒谎,于是逮捕了孩子的爸爸,可真相真的如此吗?
1988 年,一个五岁男孩无意间说出口的「童言」掀起了滔天巨浪,一桩万众瞩目的「谋杀」大案就此浮出水面。一夜之间,「杀妻分尸」、「恐怖童言」这些字眼充斥在台北市每一个角落。(一)妈妈呢?1988 年 10 月 5 日前,台北市的警察局里来了位中年女人,她焦急地左右张望着。「警官,我那可怜的女儿被杀了!」报案的女人名叫陈桂梅,她口中被杀害的女儿名叫吴瑞云。 (吴瑞云)陈桂梅在警察局里痛哭流涕,称自己知道凶手是谁,手里还有录音证据,求警方赶紧实施抓捕。台北警方一听是杀人大案,立马重视起来,陈桂梅带来的录音当即回荡在警局的每个角落。「那天晚上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就没有再看到妈妈了。」「妈妈的脚也被爸爸拿下来了,肚子里的东西,被装进了很多黑色的小袋子里。」「爸爸要我们说,妈妈跟别的男生一起走了。」录音里是一个孩子的稚嫩声音,可说出的话却让在场的警察们惊骇不已。他们意识到,这很可能是一起重大杀妻分尸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台湾警界正在经历治安历史上的黑暗期,枪击、抢劫案件不断,被捉拿归案的凶手却寥寥无几,公信力大不如前。所以面对此等大案,警方打起了十二分精神,即刻开始询问陈桂梅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想尽快破案以重拾警察尊严与威望。根据陈桂梅断断续续的描述和那段录音中的童言,一个惊人真相浮现在眼前。(二)出海归来1988 年 7 月 12 日,吴瑞云出海工作 6 个月的丈夫姚正源回家了。24 岁的姚正源是名海员,与吴瑞云育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和四岁的女儿,为了多多赚钱养家,年轻的他选择了「海员」这个时常离家、不能陪伴妻子和儿女,但收入有保障的职业。为了庆祝姚正源平安回家,平日总是看不上这位女婿的陈桂梅特意打来电话,邀请他们一家四口明日来家里好好团聚庆祝一番。 (吴瑞云与姚正源结婚照)姚正源满口答应下来,想到自己不在的时间里全靠岳母照顾妻子、孩子,肯定要登门感谢一下。然而到了第二天(7 月 13 日),敲开陈桂梅家门的只有姚正源,女儿吴瑞云和孩子却没有出现。问起姚正源原因时,他只说吴瑞云在家陪孩子,就不过来了。这让准备了一大桌子菜的陈桂梅感觉不对劲,她沉着脸给女儿打电话问究竟怎么回事,毕竟这个女婿「人一般」,这次女儿没有跟来,一定又是吵架闹别扭了。当吴瑞云接通电话后,说辞与姚正源一致,说要给两个孩子准备晚餐,就不过去了。做妈妈的陈桂梅自然心疼自家女儿,所以这顿饭吃的心不平、气不顺,草草就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陈桂梅的心因为两通电话变得不安起来。7 月 15 日,吴瑞云开口向陈桂梅借了 2000 块钱,之后就再也没有打来过电话,而这之后关于吴瑞云的行踪,陈桂梅都是从女婿姚正源的口中获悉的。7 月 16 日,姚正源忽然告诉陈桂梅,他们要从克难街的国光国宅小区搬走了,新家因为固定电话还没装好,所以暂时不能打电话,等一切整顿好了就马上恢复联系,临了还补充了一句,「岳母不必担心」。但女婿的话非但没能让陈桂梅放心,反而让她更加焦虑了。「女儿不会出什么事了吧?」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陈桂梅又在家等了两个月,但结果如之前一样,吴瑞云依然没有跟陈桂梅联系过。苦等多日之后,陈桂梅又再次给女婿姚正源打电话询问情况。这一次,姚正源干脆了当地告诉她,「吴瑞云跟我吵完架离家出走了,我已经报过警了。」一听到「离家出走」这几个字眼,陈桂梅瞬间慌乱起来,这解释太牵强了。她思索起女婿近几个月来的表现,疑窦顿生。10 月 4 日,陈桂梅又张罗了一桌好菜,借着关心孩子的名义,让姚正源带儿女来家里吃饭,饭桌上,姚正源的电话从进门起就没停过,一个接一个。见到此情景的陈桂梅当即抓住了机会,趁姚正源不在时,赶忙拉来五岁的哥哥询问妈妈去哪里了。「爸爸把妈妈的头拿下来了哦。」哥哥童稚的声音说出了这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听闻此言的陈桂梅大惊失色,两个多月的猜测在此时也得到了印证,原来是女儿遭遇了不测!为了确认外孙没有胡乱编造,陈桂梅在 10 月 5 日这天,孤身来到了姚正源所说的新家。她压抑着恐惧再次悄悄询问了两个孩子,他们的回答也变得更加具体、更加恐怖,也就是开头提及的几句恐怖童言。第二天一早,陈桂梅带着两个孩子的录音,跌跌撞撞地向警察局走去。(三)杀人凶手10 月 6 日,姚正源被警方突袭抓捕。在幼儿园门口等候两个孩子放学的他,在上警车前一阵挣扎,引来了不少围观者。面对警方多次的审问,这个皮肤被海风吹得发红的男人一脸惶恐,瞪大了眼睛。「不是我,我没杀人!吴瑞云肯定没死,她要离婚就离,我也不至于杀人。」见姚正源不承认自己的罪行,警方放出了两个孩子的录音。听完之后,姚正源像疯了一般大喊「冤枉」,表示自己从 7 月15 日起就没有再见到过吴瑞云,之后的日子一直在做水电零工,同时也会去跑跑出租,直到被警方突然抓捕。而在警局之外,「杀妻」「分尸」「恐怖童言」这些劲爆的字眼,瞬间传到了台北市的每个角落,当地媒体更是争相报道这起「恶男杀妻事件」。 (当时的媒体报道)一夜之间,姚正源等于「恶魔」的说法喧嚣而起,各种谩骂和猜忌如潮水般涌来。母亲陈桂梅更是声泪俱下,向媒体四处哭诉姚正源的残暴和女儿吴瑞云的可怜。就连住在姚正源夫妇旧址的房客,也向大众讲述自己的惊悚经历——「我梦到一个断头女,穿着红衣,满地都是血。她也不说话,就默默看着我。但我觉得,她肯定是被害死的。那人,除了她老公还能有谁?」这位房客还说,自己入住时曾在冰箱里发现一袋用硬塑料纸包裹的腐肉,已经生蛆了,臭气熏天,不过那袋腐肉早就被丢弃了,无处可寻。人们纷纷猜测着,冰箱里的腐肉想必是吴瑞云残缺的尸体。惨死的吴瑞云让人唏嘘不已,所以在姚家原先居住的克南街上有人为吴瑞云设了一座灵堂,供人拜祭,以慰冤魂。 (坐落咋克难街的灵堂)然而对于姚正源的调查和审讯,却陷入了僵局。因为不论采取哪种形式审问姚正源,他都坚称自己没有杀害吴瑞云,并一口咬定是岳母陈桂梅从他与吴瑞云结婚起就不喜欢自己,一定是她故意指责陷害。见过大风大浪的警方当然不会相信他的话,毕竟姚正源身上疑点重重。比如姚正源一直声称吴瑞云在一家电子厂上班,可在警方排查后发现,吴瑞云根本没有在电子厂上班,而是在一家三温暖店工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浴桑拿店)。作为一个丈夫,怎么会不清楚自己妻子在哪里工作呢?还有,姚正源突然搬家的行为也引起了警方怀疑,在原先小区住了很多年的姚家夫妇,为何会在姚正源出海归来的三天后,迅速搬家离开了呢?难道是为了隐藏或躲避些什么? (姚正源的新住所,桃园龙潭)带着这样的疑问,警方与法医迅速前往姚正源的新、旧住所,可惜的是,现场既没有任何血迹反应,也没有找到作案工具。这也说明吴瑞云被杀害或者分尸的第一现场,都不在家中。如果没有找到吴瑞云的尸体和实质性物证,姚正源就不能被定罪,于是警方改变了调查方向,他们开始从姚正源可能埋尸的地点着手,展开排查。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新转变让警方从姚家小兄妹口中得到了一个爆炸性的新线索。当警方试探性询问两个孩子爸爸的行踪时,发现他们竟然可以详细地描绘出姚正源埋尸的地点和具体过程。「早上的时候,爸爸开着计程车带我们两个到了青年公园跑马场附近。之后我们就被锁在了车里,隔着窗户,我们看到了爸爸挖了一个大洞,把妈妈埋了进去。」尽管这种让孩子二度回忆恐怖画面的做法受到了众多专家和民众的抨击,但结果仍是让警方兴奋不已。真相,仿佛就在眼前。然而在大家掘地三尺几个小时后,万众期待的结果却没有适时出现,孩子口中的「尸体」根本不存在,甚至连一根人类的一根头发丝都没有找到。因为这次「兴师动众」的出警,直接将警方推至风口浪尖,让本就所剩无几的公信力不升反跌,惹得众怒连连。人们也不禁发问,两个年幼的孩子所说的证言到底能不能采信?(四)反转来袭从青年公园回来后,台北警方陷入了巨大疑惑之中。一面是姚正源坚称自己冤枉,一面是真假难辨的恐怖童言,案件就此走进了死胡同。就在警方苦苦寻人之时,几位证人的出现打破了僵局。起初,一位吴瑞云的好友站出来称自己在 8 月份还见过吴瑞云,怎么可能在 7 谁被分尸呢?紧接着越来越多的目击者出现,最后发现竟然有五个人分别在 8月份、9 月份见过吴瑞云!与此同时,一个自称吴瑞云本尊的人也突然打来一通电话,说自己没死,只是不方便出现,让警察不要再找了。然而当警方邀请她出面澄清时,女子却果断拒绝,迅速挂掉了电话。警方判定,这是一个恶作剧。公众的议论喧嚣直上,警方的压力日益增长,他们越来越怀疑录音里那段童言童语的真实性。故而当时的检察官管高岳在侦查庭上,以配合调查为由将陈桂梅支走,再次轻声询问那对备受瞩目的小兄妹。「爸爸杀了妈妈吗?」「不知道……」听到这个回答,检察官屏住了呼吸,接着又问,「是有人教你们那样讲的吗?」在静静等待几秒之后,4 岁的姚家妹妹终于对着检察官点了点头。这个「教」孩子说谎的人,就是陈桂梅。对此,台北警方邀请来了儿童心理专家来分析姚家兄妹的「翻供」行为,专家称「从心理研究学的角度来说,儿童的想象力是丰富的,有时他们会无意识得编造事实,也会在被刻意引导后展开联想。」由于姚家兄妹翻供,所以之前所有的指证都不再具有可信度,再加上没有找到案发现场、尸体、作案工具等实际证据,被关押八天的姚正源被无罪释放。从警局离开时,姚正源对警方说,两个孩子一定是被岳母陈桂梅唆使说谎的,因为陈桂梅不是第一次状告他杀害妻子了,在两三年前,因为吴瑞云离家出走一个月,陈桂梅就曾大张旗鼓地指责姚正源杀了女儿。事已至此,「恶男杀妻分尸案」反转成了一桩「普通失踪案」。面对教唆孩童说谎、扰乱警方办案的指控,陈桂梅大呼冤枉,说自己也是被两个孩子骗了。由于线索太少,案件就此被搁置,吴瑞云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直到三年后,这起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件重回公众视线,风波又起……(五)鬼神之说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被冤枉的姚正源在关押期间收到的漫天辱骂,在他无罪释放后并没有停止,很多人依然坚定地认为是他杀害了妻子,姚正源社会性死亡。更雪上加霜的是,小女儿因为一场车祸,住院了。近几年来一直在跟进这起「杀妻案」的记者,看到姚家小女儿住院,立马兴奋了起来。试想,一个母亲如果看到自家女儿车祸住院,必然会马不停蹄地来到孩子身边。记者们看准了这一点「母爱本性」,在医院外日夜蹲守,等着吴瑞云亲自现身后立马安排头版头条。然而直到小女儿痊愈出院,众人期待的那个「母亲」也并未现身。不论是警方、媒体还是当地民众,都认为到如此关头仍不出现的吴瑞云,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而陈桂梅这边,虽然涉嫌指示姚家小兄妹作伪证,但她那一颗爱女的心,却比金子还真。在案子被搁置的三年间,陈桂梅仍在坚持不懈地寻找女儿,走过了无数城镇和角落。渐渐得,陈桂梅开始放弃常规寻人办法,竟然出乎意料地借用起了「天道」,时常宣称女儿已含冤而死,曾看见女儿的卧室里有烟灰缸、钱币这类东西飞来飞去。 (陈桂梅声称从吴瑞云卧室「飞」出的钱币。)最轰动的一次是陈桂梅花大价钱请来的「著名」神婆,竟然帮她找到了女儿吴瑞云的尸骨!喜出望外的她马上让警方配合寻找自己的女儿。正常来说,警察破案依靠的是证据、是科学,但这次台北警方却参与到此次莫名的鬼神之说中。当时的警政署长庄亨岱一心想要快速破案以挽回颜面,所以亲自带队来到了神婆所指的藏尸地点。桥下人头攒动,人们好奇得来回穿梭,大家都想知道,上天会不会可怜这位思念女儿的母亲。年轻的警察们挥舞着锄头,大有几年前青年公园掘地三尺的架势。 (警方在寻找「尸骨」的媒体报道)在桥下的淤泥被挖掘了两三圈之后,警方果真挖出了一具白皑皑的尸骨。陈桂梅大惊,立马瘫坐在地上痛哭起来,大喊着「女儿好惨啊!」。警政署长庄亨岱紧皱着眉头,马上派法医将尸骨带回去检测,驱散了围观群众。然而,当人们都以为这桩长达五年的「命案」终于有了结果之时,反转再次上演。经法医鉴定,那具尸骨不属于人类,是猪骨。三年前因轻信孩童之言而备受指责的台北警方,三年后彻底颜面扫地。吴瑞云失踪案再次被搁置。(六)意外现身时间来到 1993 年的 2 月,一个年轻女子来到花莲警局,说是给自己孩子上户口。她神情畏缩,仿佛在惧怕着什么。紧接着,「吴瑞云」三个字赫然出现在警察面前的登记簿上,在场的所有人都怔愣不已。查证后发现,这女子正是「杀妻分尸案」的主角、当年挖地三尺也没有寻到的吴瑞云!这么多年来,她跑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连孩子出了车祸,作为母亲的吴瑞云都始终没有现身呢?经过审问,吴瑞云这才羞愧地交代,当年自己根本不是离家出走,而是和人私奔了。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姚正源赌气出海工作,在家里独守空房的吴瑞云耐不住寂寞,去了一家名为七吉三温暖的桑拿会所上班,而在跟姚正源的通话中,她谎称自己找了份电厂的工作。在三温暖会所里,吴瑞云结识一位杨姓男子,寂寞的她仿佛又重拾了爱情,没过多久,他们相恋了。在姚正源出海归来后,吴瑞云顿时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了依靠,跟母亲陈桂梅借了笔钱,与杨姓男子私奔了。乌龙事件闹大后,吴瑞云不是没有想过澄清,那通说吴瑞云没死的电话,就是她亲自打给警方的,然而胆小自私的吴瑞云不敢亲自出面澄清,因为杨姓男子对她的过往一概不知!原来,从认识杨姓男子第一天起,吴瑞云就动了心思,对外一直谎称自己名叫刘瑞莲,她的现任「丈夫」根本不知她有家有室,甚至连姓名,都是假的。她此次之所以现身,实属万不得已,因为她和杨姓男子有了孩子,这个孩子到了年纪要上学,而上学就需要有合法的户口。若不是因为这个,自私的吴瑞云也许永远不会现身,「杀妻分尸案」也会变成一桩悬案。(七)一点想法纵观整个案件的发展,我的第一观感是:荒诞。吴瑞云自私自利,抛夫弃子离家出走,不论事态如何发展都不现身,这是荒诞之一。母亲陈桂梅思女心切,教唆外孙指认女婿杀妻,这是荒诞之二。台北警方在案件调查中主次不分,想依靠孩童证言与鬼神之说快速破案,这是荒诞之三。正是因为以上三方面的离谱之处,导致了一场长达五年的大乌龙事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姚家两个孩子的「恐怖童言」,这在当时社会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一、致命的童言「小孩子才不会撒谎。」正是秉承着这一浅显的认知,警方逮捕了姚正源,民众开始了无限猜疑与攻击。我们很难想象,如果吴瑞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如果两个孩子的证言没有被推翻,那无辜的姚正源的后半生,会不会永远背负着「杀妻」的嫌疑,永远活在谩骂里?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2018 年的安徽淮北,一名五年级男生向父母谎称自己被老师殴打。第二天,男生的父母联系了八位亲属一同赶往学校,在见到老师的第一瞬间,男生的妈妈与小姨致直接就把老师按到了墙角,一边撕扯头发一边殴打其他部位。最后,说谎的男生承认自己撒谎,他的父母被处罚拘留 15 日,而这位勤勤恳恳的老师却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体与精神受到了极大打击。这些都让我想起了一部丹麦电影,《狩猎》。主人公卢卡斯是个善良温和的中年男人,离婚后的他找了份幼儿园的工作,因为性情温和,耐心负责,园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有些早熟的五岁女孩卡拉也不例外。当卡拉对卢卡斯产生好感后,不仅亲手制作了心形的小礼物塞到卢卡斯包里,还扑过去亲吻了他的嘴唇。面对卡拉的示好,卢卡斯当然是拒绝的,还让她把心形小礼物送给其他小朋友,这让卡拉备受打击,她决定报复这位老师。 (电影剧照,主人公卢卡斯)当天晚上卡拉就去找院长倾诉,卢卡斯对她进行了「性侵」。之后,卢卡斯的工作被无限期暂停,儿子打来电话质疑他、前妻专门来讽刺他、好朋友与他划清界限,自家狗狗甚至被恶意毒死、所有人都开始指责卢卡斯……更加荒唐的是,当警察与园方询问其他小朋友时,他们的答案竟然与卡拉惊人的一致。可面对漫天的谣言,卢卡斯的解释太过苍白和无力,没有证据,容不得辩解,一句「小孩子不会撒谎」让他在短短几天内「社会性死亡」。这是不是像极了被冤枉了的姚正源?到了影片最后,卡拉承认自己撒了谎,捆绑在卢卡斯身上的枷锁终被卸下,但一切都结束了吗?没有,枷锁仍在,甚至更加沉重。当卢卡斯站在 10 月的北欧森林里,享受重见天日的幸福时,从远处突然传来一声枪响,一枚子弹与他擦肩而过!二、集体的撒谎行为结合吴瑞云案与电影《狩猎》,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在孩子间会出现集体撒谎的情况?比如姚正源的两个孩子口径极为一致地指认爸爸杀了人。再比如卢卡斯所在幼儿园的孩子们,他们可以详细地描述出卢卡斯家里的地下室位置、墙壁、沙发的颜色,表示自己也曾被性侵。但实际上,杀妻分尸根本没有发生,卢卡斯家里也没有地下室。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曾经做过一个有关「从众行为」的实验,参与实验者是 123 位大学生。每组 7 人同时参加考试,其中只有 1 人是真正的被试者,其余6 人都是「演员」。被试者被安排在倒数第 2 个回答问题,这样他可以听到大部分不正确的回答。阿希为实验准备了 18 套试题,每套两张,一张绘有标准线段,另一张绘有比较线段,被试者需要在右图的 abc 选项中选出比左图短的选项。 (阿希实验内容示例,答案其实显而易见。)在实验过程中,卡片共出现 18 次,但从第 7 次开始,「演员」们开始故意选出错误答案,以此来观察被试者的从众心理和个体独立性。实验结果表明,约有 75% 的被试者至少有一次从众行为的发生;25% 到 33% 的被试者没有被其他人所影响,保持了独立的判断;所有被试者的平均从众行为 34%。在实验结束后的询问中,被试者普遍反映在实验中感受到了严重的心理压力和内心冲突。因此我们可以试想,群体压力之下的成年大学生都会有从众行为,更何况总是希望「和大家一起玩耍」的小孩子们呢?在充满谎言的洪流中,说真话的人往往是被边缘化的那一个。It's always assumed that children tell the truth. Andunfortunately, very often they do.我们总假设孩子们不会撒谎,但可惜,他们经常撒谎。——《狩猎》金榜题名的意思解释?
答:金榜题名的原意来源于旧社会的科举制度,通过最高的殿试考中的举人名单称为金榜,在金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就是金榜题名。
